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唯美主义者和颓废主义者,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斯坦尼斯洛斯·埃里克·斯坦博克伯爵(Count Stanislaus Eric Stenbock)和伊诺克·索姆斯(Enoch Soames)等人,在张扬他们不羁的个性、蔑视资产阶级权势的同时,为了艺术的原因赞美和歌颂艺术。这些优雅的年轻人写出了超凡脱俗的诗歌和散文,给它们起了诸如《不和谐》(Discords)、《残骸》(Wreckage)和《否定》(Negations)等题目。那是声名狼藉的十九世纪英国文艺季刊《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时代,也是奥布里·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描绘的奇异怪诞的小丑和交际花的时代。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也是现代同性恋文化首次开花结果的时代。
尽管1890年代涌现出了许多有着奇怪个性的人物,但没有比弗雷德里克·威廉·罗尔夫(Frederick William Rolfe)更奇怪的了。1904年,罗尔夫用拜伦·科尔沃(Baron Corvo)这个笔名,写了一部惊心动魄的小说《哈德良七世》(Hadrian VII),书中写到格拉布街(Grub Street,伦敦的一条旧街,位于西区莫费尔德,过去为穷苦潦倒文人、新闻记者和出版商的聚居地,也是英国出版业的一个中心——译注)的一个落魄文人被选为了教皇。罗尔夫本人是一个非常粗鲁、既偏执又心怀恶意的人,正如人们从A.J.A.西蒙斯(A.J.A. Symons)在1934年为罗尔夫撰写的传记《探求科尔沃:一部实验性的传记》(The Quest for Corvo: An Experiment in Biography)中了解到的那样。这本传记最近由塔塔鲁斯出版社(Tartarus Press)再版,被编撰成了一个漂亮的附有插图的版本,由马克·瓦伦丁(Mark Valentine)写了精彩的介绍。在书中,我们不仅能读到罗尔夫丑闻缠身的过往生活,其中最离谱的,要数他与威尼斯贡多拉船夫的嬉闹作乐,还能读到西蒙斯在为这部难以驾驭但却引人入胜的传记收集写作信息时,与一些古怪的收藏家和年迈的牧师进行的访谈。
因此,这本传记记录了两个人的身影,文笔优美,字里行间充溢着古典魅力,具有诱人的可读性,被誉为次杰作(minor masterpiece)。但是,说真的,难道不正是这些次杰作才是最棒的吗?正巧,纽约格罗里埃藏书俱乐部(Grolier Club)而今正在举办一场名为“A.J.A.西蒙斯:一位藏书家,他的书和他的俱乐部”(A.J.A. Symons: A Bibliomane, His Books and His Clubs)的展览,展览将延续至2019年1月5日。对于爱书人来说,去一趟曼哈顿是值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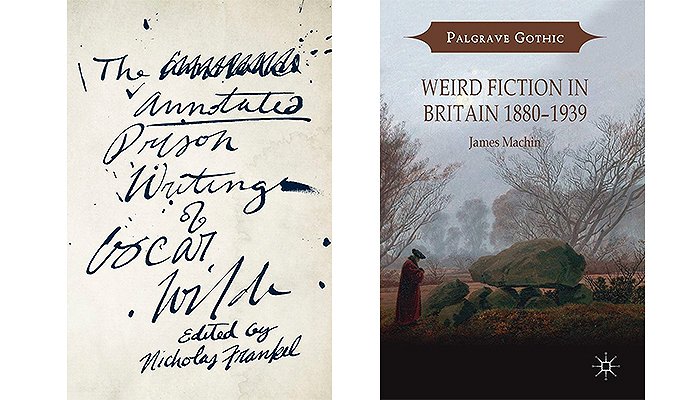
2018年初,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尼古拉斯·弗兰克尔(Nicholas Frankel)编辑的《注释版奥斯卡·王尔德的狱中笔记》(The Annotated PrisonWritings of Oscar Wilde),弗兰克尔曾为原始版本的《道林格雷的画像》做过注释。王尔德与年轻男子过往频密,因严重猥亵行为罪被判入狱强迫劳役两年,当时无比沮丧消沉的他仍然顽强地写出了生命后期的重要作品,包括《雷丁监狱之歌》(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和《自深深处》。《雷丁监狱之歌》里令人难以忘怀的句子一直流传至今,如:人人必杀所爱,因此人人得以苟活。《自深深处》是1897年王尔德写给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中篇小说长度的书信集(在此书中,诗人气质的作家首次写出了“不敢直呼其名的爱”这样的语句),在书中,又名囚徒C33的王尔德回顾了他与道格拉斯缠绵纠结的感情关系,以及因这场同志爱恋(他曾经充满挑逗意味地称之为“与美洲豹的尽情欢宴”)被公开而蒙受的耻辱,之后两人中较为年长的王尔德的人生彻底跌入毁灭深渊。
1890年代,王尔德的爱尔兰同胞威廉·巴特勒·叶芝(W.B.Yeats)在伦敦度过了大部分时光,后来他在“韵客”俱乐部(Rhymers Club)纪念他的朋友时,将他们称为“悲剧的一代”(the tragic generation)。这些人之中,32岁就去世的诗人厄内斯特·道森(Ernest Dowson)也许是后来最出名的一位,他的名作《辛娜拉》(Cynara)中那些发自内心呼喊的诗句令人难以忘怀:”辛娜拉,我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忠诚地爱着你。”而叶芝本人最为钦佩和崇拜的是诗人莱昂内尔·约翰逊(Lionel Johnson)。Strange Attractor出版社将于2019年1月出版一本由尼娜·安东尼娅(Nina Antonia)编辑的新书:《无可救药:颓废时代的黑暗天使——莱昂内尔·约翰逊焦虑不安的著作》(Incurable: The Haunted Writings of Lionel Johnson, the Decadent Era's Dark Angel),一篇题为《仪式般的吸引力》(Ritualistic Adorabilities)的文章是这本新书的序言,也是对这位诗人一生最好的简要概括。约翰逊是一位身材矮小,长相可爱的男士,在古典文学方面学识渊博,曾是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情人(直至王尔德出现),一贯嗜威士忌如命,也非常迷恋被称作“绿魔鬼”的苦艾酒,35岁时死于长期酗酒引起的中风。他的一生令人联想起他的诗句:“离开我罢,我是那些堕落的人之一。”
至于奉行颓废主义的颓废者斯坦尼斯劳斯·埃里克·斯坦伯克伯爵(Count Stanislaus Eric Stenbock),谁又能说些什么呢?他的诗歌和散文(如今已不容易找到)都收集在由大卫·悌别特(David Tibet)编辑、Strange Attractor出版社出版的《国王与万物》(Of Kings and Things)一书中。斯坦伯克是一位爱沙尼亚贵族,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是一名同性恋,同时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吸食鸦片严重上瘾。他的作品包括:由各种病态和浪漫故事组成的《死亡研究》(Studies Of Death)、一个关于蓝花(blue flowers,是德国浪漫主义艺术理想的最高象征,其核心含义是注重想象、渴望心灵自由与灵魂安宁——译注)且风格与德国浪漫主义小说家E.T.A.霍夫曼(E.T.A. Hoffmann)类似的黑暗童话故事,名为《另一面》(The Other Side),以及三卷忧郁的诗歌:
那双眼睛!我不敢直视,
嘴唇!我不敢触碰——
你会为我祈祷吗
是谁,日夜都在为你祈祷?
斯坦伯克的《吸血鬼的故事》(The Story Of A Vampire)是被最多文集选入的散文作品,与其说这是一个恐怖故事,不如说是对同性恋或乌拉尼亚式(Uranian,那个时代更喜欢用的词,指第三性别的人,乌拉尼亚是主管天文的女神,九大缪斯之一——译者注)的爱与死亡(Liebestod,源自德语)的隐晦描述:为了生存,饱受折磨的瓦尔达克伯爵(Count Vardalek)必须杀死他深爱的、长得像弗恩(Faun,古罗马传说中半人半羊的农牧神——译注)的男孩加布里埃尔(Gabriel)。斯坦伯克35岁去世之前,据说他带着一个儿童大小的木制玩偶旅行,而且把这个玩偶当作真人对待,亲昵的程度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或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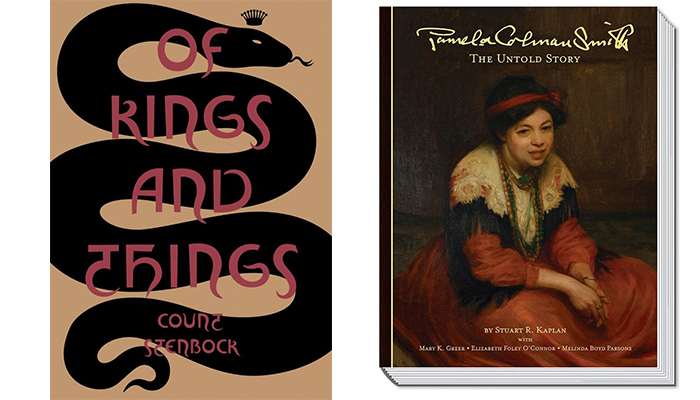
喜欢了解各种知识的读者绝对应该去找出詹姆斯·麦钦(James Machin)的《1880-1939年英国怪异小说》(Weird Fiction in Britain, 1880-1939)来读一读,这本书使恐怖小说重新被纳入了世纪末的经典著作行列,沿着其中隐伏的线索,读者可以继续进行一些相关的阅读,例如以前的美国低俗杂志《怪诞故事》(Weird Tales)等。阿瑟·马臣(ArthurMachen)的中篇小说《潘恩大帝》(The Great God Pan)里充斥着越界的性行为,而M.P.希埃尔(M.P. Shiel)的小说《火焰中的形状》(Shapes In The Fire)则是以一种狂热且过度修饰的散文似的文字写成,显然是陶醉于诗人斯温伯恩(Swinburne)曾经描述过的“罪恶的狂喜和玫瑰”。
在引人入胜的《帕梅拉·科尔曼·史密斯:不为人知的故事》(Pamela Colman Smith: The Untold Story)中,四位学者斯图尔特·R.卡普兰(Stuart R. Kaplan)、玛丽·K.格瑞尔(Mary K. Greer)、伊丽莎白·弗利·奥康纳(Elizabeth Foley O'Connor)和梅琳达·博伊德·帕森斯(Melinda Boyd Parsons)共同描述和赞扬了这位重要的图书艺术家和戏剧服装设计师及其职业生涯。帕梅拉·科尔曼·史密斯与1890年代的神秘学家A.E.韦特(A.E. Waite)一起为现代莱德-韦特塔罗牌(Rider-Waite Tarot)设计了插图,因此她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T.S.艾略特(T.S. Eliot)的算命师索索斯特里斯夫人(Madame Sosostris)显然是使用了史密斯那副“邪恶的纸牌”,因此艾略特得到了这么一句训诫意味的最后忠告:“我没有找到倒吊人牌。小心死在水里。”
(翻译:郑蓉)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